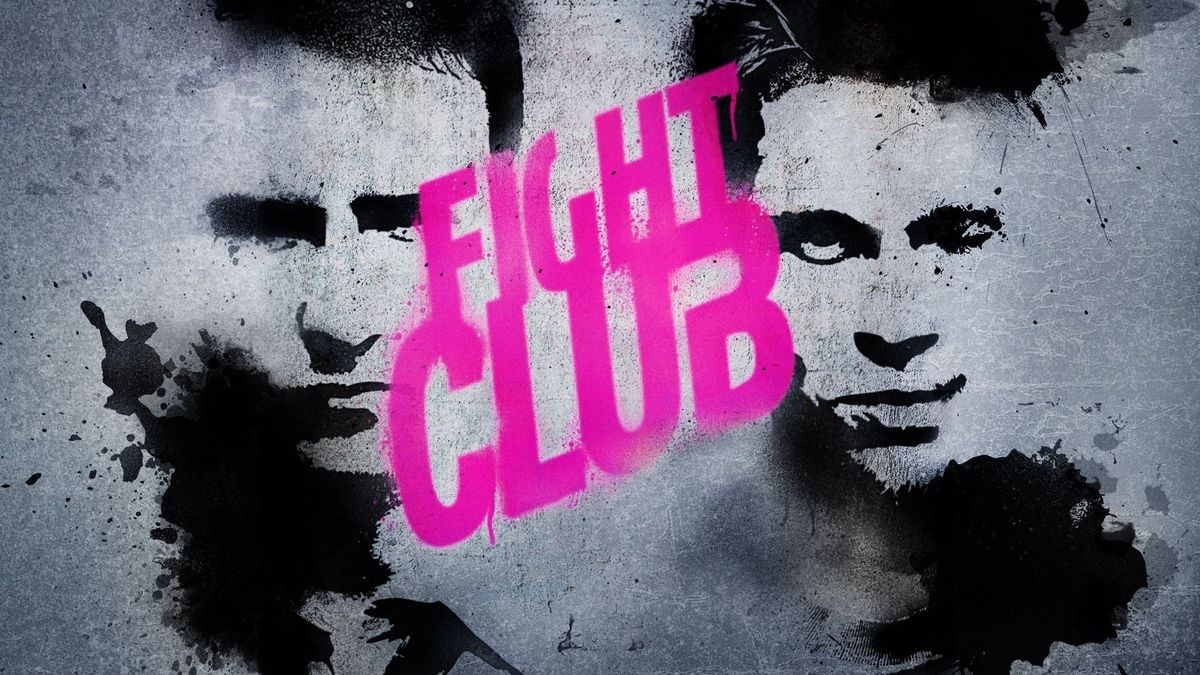《鬥陣俱樂部》繼續在爛泥擱淺還是摧毀一切? 劇透
身處於世界末日的人會怎麼面對自己的人生?1990是奇才橫空出世的年代,世紀末的威脅讓所有人感受到末日將至的危機,於是像煙火一樣,迸發出許多後代難以超越的作品:《猜火車》、《美國心玫瑰情》、《春光乍洩》、《情書》、《駭客任務》……名單還可以一直列下去。那個時代雖然有著面對盡頭的焦慮,卻是許多奇蹟作品的盛世年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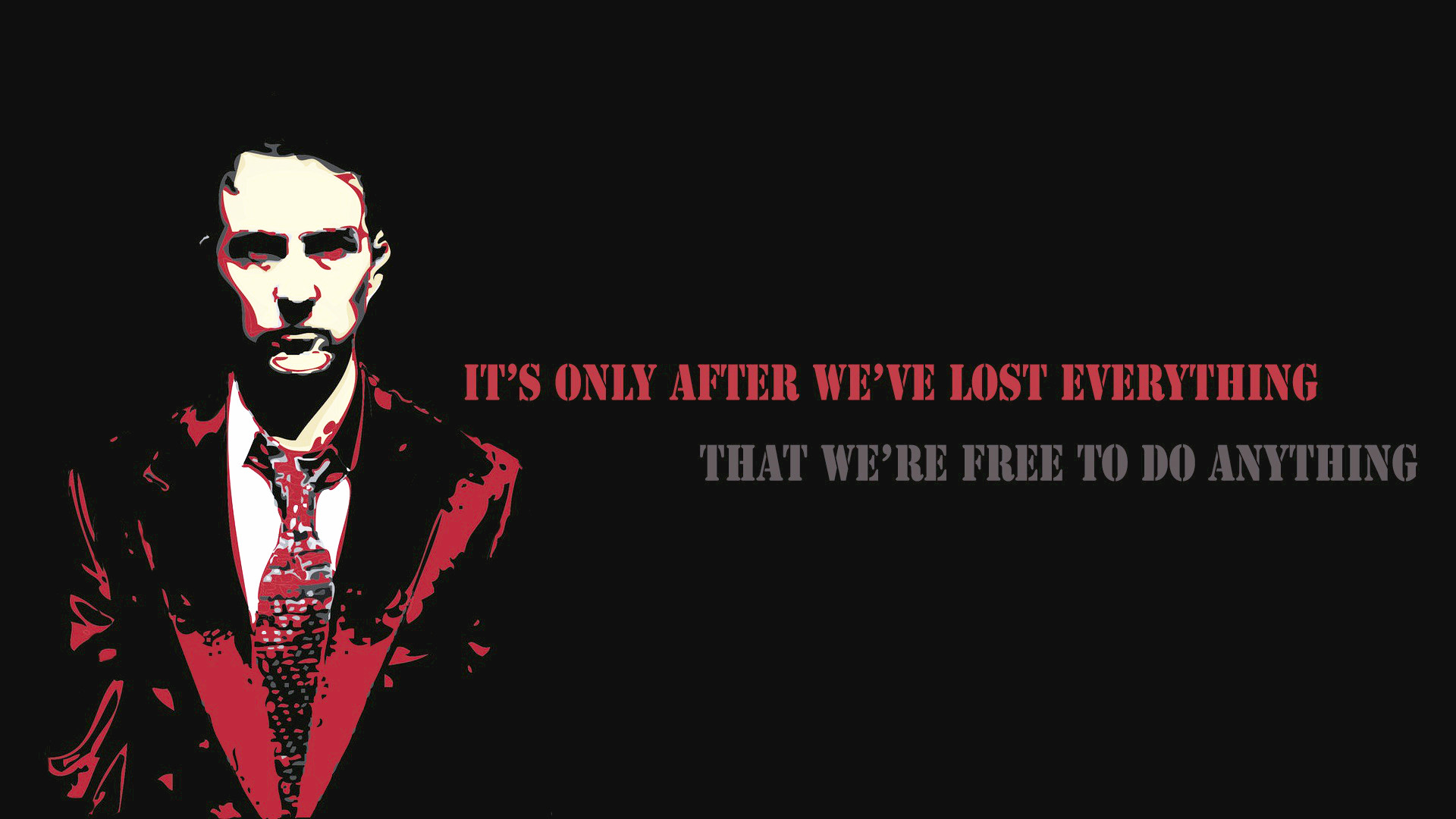
《鬥陣俱樂部》也是部擁有強烈末日指涉的作品,以一個連名字都曖昧不清的主角(Edward Norton 飾演)為主要敘事者,第一人稱獨白的方式帶出了頹唐空虛卻又狂放不羈的獨特氛圍。導演大衛.芬奇在片中馳騁各式各樣的奇思妙想,有些電影拍攝手法甚至已經脫離了正統,而帶有邪典(cult film)的實驗性:大量運用跟拍式運鏡(Follow shot,讓鏡頭跟在主角前方或背後一起移動,帶出臨場感)、極限特寫鏡頭(以非常近的距離特寫某項物品,再慢慢拉遠,帶出場景),並且靈活地運用蒙太奇手法,讓影格與影格之間的擁有強烈的暗示象徵性。加上挑戰讀者容忍度的極限主題、拉近距離的後設手法,以及片中到處藏匿的小彩蛋,讓這部電影有著難以言喻的魅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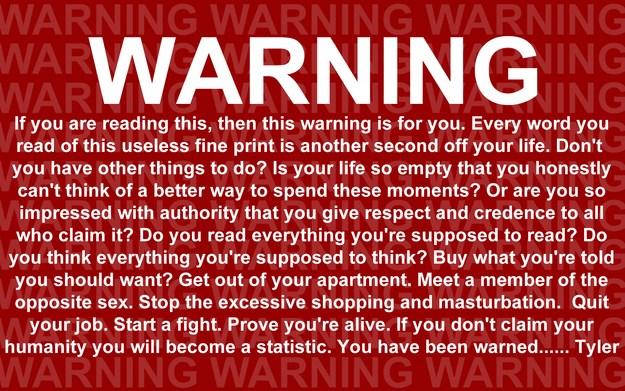
導演的彩蛋之一,出現在片頭,泰勒對觀眾說的話
初遇的觀眾大概不會立刻接受這部片,甚至下意識地抗拒排斥,但《鬥陣俱樂部》總會在心裡如同幽魂一樣縈繞不去。這部片起初上映時,並未在一開始就獲得好評,甚至當年奧斯卡的提名,也僅入圍了音效剪輯獎而已。然而隨著DVD的推出,《鬥陣俱樂部》漸漸受到觀眾的歡迎,最後甚至成為一部足以代表1999年的年度電影。
為何《鬥陣俱樂部》會有這樣獨特的先拒絕後熱愛的觀影經驗?很有可能是因為,這部電影直率近乎張牙舞爪地指出了那些我們避開目光不看,卻確實存在我們內心的某些心境。不論是世紀末的當時,或是「後世紀初」的現代,我們這些時時面對著終結與起初的人們,在這個「美麗新世界」,用各式各樣的物質來填補,好假裝自己活得篤定而安穩,最後卻仍然無法否認這個事實。
活在不斷消費的「美麗新世界」裡
「美麗新世界」這個詞不是我的比喻,而是借用赫胥黎《美麗新世界》的反烏托邦世界。在那個世界裡,人們因為快速而頻繁更新的資訊而失去了關注能力,被大量的消費廣告洗腦,因而不斷重複購買集體式的娛樂行為,因而達成了和諧的愉悅社會。這是世紀末的生活,也是現代的我們的生活,但總會在不斷不斷持續地消費之後,內心終究會浮現主角所感受到的:
「一切都好空虛,都成了相同的拷貝的拷貝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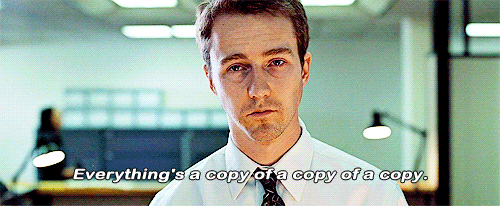
主角對觀眾獨白,以前他是看色情圖片找刺激,現在是看郵購目錄。他迷上了家具裝潢,看著型錄想像到底哪種家具能夠代表我這個人。他絕望地對觀眾自白:
「我們滿腦子想的都是物質。」
除了物質,除了購買與消費之外,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?檢視自己的心,發現空空如也的主角,終於開始失眠。他六個月無法闔眼,因為實在無法說服自己,每天做著道德淪喪的工作,購買能力所及的奢華物品,對自己來說,究竟還有什麼樣的意義?他所追尋的意義,也是我們想要問自己的。就算外表再怎麼富麗堂皇,內心也是一片蠻荒,刺激所造成的終究是愉悅的快感反應,那不會是填補生命中空缺核心的意義。主角就是我們所有人,所以他有時被叫做傑克,有時被叫做別的,每一次他身上別的名牌都不是相同的名字。失去了自己的自我認同,叫什麼名字都沒差,不是嗎?
以死覺生,與絕望恐懼共存
所以主角開始尋求別的管道,有些別的「什麼」能夠讓自己不再空虛,得到安寧,整部《鬥陣俱樂部》其實也是在尋找這樣「填充核心」的過程。面對現世的意義缺乏,主角找到了一個詭異的出口:他開始尋訪各式各樣的絕症互助團體:睪丸癌、肺結核、皮膚癌、腦瘤,進入這些因為疾病而產生共同連結的人群中,主角感受到「黑暗、沉默和完整」,畢竟快死的人說話特別有份量,別人不敢打斷,因此才能夠好好地說一段話,好好地擁抱一個人,主角說
「我每晚都會死一次,可是又重生一次,復活過來。」
面對盡頭的恐懼,一切事物會變得清明,恐懼會澄清所有雜訊與執迷,讓自己無比清晰地察覺自己「正在活著」的當下。由於一同面對著生命盡頭,互助會的人比起外面的人擁有更多的親近連結,畢竟同是將赴死之人,這是每個面臨末日的人,都會有的惺惺相惜之情,於是面對切除睪丸導致女乳化的病友鮑伯(Meat Loaf飾演),主角這麼說:
「我靠著他的奶子準備哭泣,這簡直就是假期。」

雖然荒謬到讓人失笑,但那畢竟是空無一物的內心,可以裝填的莊嚴事物。因為死亡而感到活著,多麼諷刺,卻又多麼充實,但畢竟1999年並不是真正的末日,主角也沒有真正的絕症,憑藉著虛假的死亡預兆是不可能度過人生所有坎坷的。察覺這點,是主角遇到了瑪拉(Helena Bonham Carter 飾演),那個與自己有著共同秘密的女人。主角發現,只要有瑪拉,他就無法真正進入面對死亡的安寧中。他跟瑪拉開始爭奪著參與聚會的權利,睪丸癌給你,但我要腦癌。這些不吉利的,與死亡有關的疾病,成為了瑪拉與主角的珍視之物。他們圖的也就是一點絕望,被動地接受絕望好獲得盼望,追逐黑暗好得到光明,在這條二律背反的道路上,註定沒有出口。
以棄換得.讓怒火導航人生
所以當主角開始在每次航程期待自己因為意外而墜機或是爆炸,想像終末的場景,觀眾就該知道,想像盡頭,想像死亡,想像恐懼與絕望,再也無法召喚那些清明知覺與希望盼望了。人生是窮途,但還不是末路,再怎麼渴望地被動等待,末日都不會前來,所以泰勒(Brad Pitt 飾演)出現了。他一派佻㒓奔放,問主角:
「你會變成不同的人嗎?」

泰勒也看穿了主角的笑聲帶著絕望,因為泰勒,主角捨棄了被動地依賴死亡帶來的末日感,放棄公寓還有物質生活,放棄依賴讓人安寧的現狀。既然人生就是一灘爛泥,為什麼我們還要好好對待自己這個擱淺的人?在一次試煉中,泰勒把強鹼倒在主角手背上,一邊讓他感受灼熱的痛楚一邊對他說著:
「你要假設上帝不愛你。
他一直都不愛你。
你的痛不是最悲慘的事情。
去他的詛咒和贖罪。
我們是上帝被遺棄的子民。
你得先放棄一切。
你必須沒有恐懼。
只有拋棄一切,才能獲得自由。
恭喜你,你越來越接近極限了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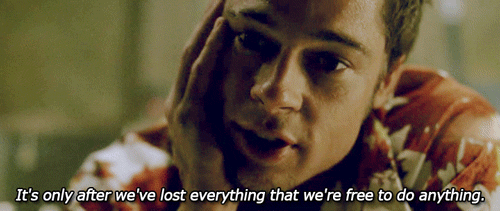
拋棄了這狗屎爛蛋的人生,最後只剩下毀滅的憤怒衝動。人生唯一需要培養的是「看透並且拋棄,不在乎失去一切」的能力,再也不需要「在大奶子上哭泣,在大奶子上窒息。」如此卑微地活著,憤怒然後反抗,拋棄一切才能得到新生,這就是「鬥陣俱樂部」成立的宗旨。不允許對別人談論的「鬥陣俱樂部」,是以自毀為前提的組織,在俱樂部的自己不是其他地方的自己,因為其他地方都必須扮演積極向上的自己,只有在這裡才得以墮落。我們的空洞就在我們緊抓著許許多多東西不放:
「廣告誘惑我們買房子車子。沒有目的,沒有地位,沒有戰爭,沒有經濟大恐慌。我們的大戰只是心靈大戰。我們的恐慌是我們的生活,那是我們漸漸面對的現實,所以我們非常憤怒。」

因為這些擁有越多反而失去越多的憤怒,讓鬥陣俱樂部的會員們除了自毀,也要狠狠嘲諷這個世界。他們把抽脂診所的人體脂肪製成肥皂,再讓那些抽脂的消費者買回自己的脂肪;他們在菜餚裡面加料,在湯裡面撒尿。藉著拋棄這世界上的一切,取得人生的主導權。這是一場奪回人生主權的戰鬥,如果把自己的核心讓渡給了死亡跟恐懼,人生剩下的也就只是為了將到來的盡頭作準備,再怎麼樣都是被動的,但憤怒不是,憤怒會讓主角主動喊著:
「工作不能代表你
銀行存款不能代表你
你開的車不能代表你
皮夾裡的錢也不能代表你
你只是平凡眾生裡的一個
就像是準備升空的猴子
你跟其他生物一樣是個有機物。
跟其他生物沒有其他差別。」

怒火摧毀了自己,摧毀了整個世界,從「鬥陣俱樂部」升級到「大破壞行動」,毀滅格局的提昇,也就說明著對這個世界主宰控制的提昇。不論是被動地等待或是主動地毀滅,最後的結果都是末日,是盡頭,是終點,但選擇了絕望或是憤怒,就決定了自己是要繼續擱淺,還是要自行了結。
一個人兒兩盞燈
從前面的劇情一路演變至此,可以發現《鬥陣俱樂部》的對立性:被動與主動;絕望與憤怒;被毀與毀滅;拋棄與獲得,這個二律背反的特性,其實是電影試圖保持的危險平衡,因此當最後結局揭露,觀眾發現《鬥陣俱樂部》其實是部玩弄了敘述性詭計的作品時,那種二律背反性也會格外強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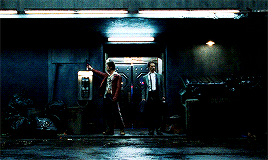
平衡在最後終被打破,其實主角與泰勒是同一個人。雙重人格的主角渴望自己變成不同的人,所以開始打造屬於自己的角色。在泰勒出現之前,在飯店的歡迎節目裡,在辦公室主管的後面,泰勒的身影都像鬼魅般一閃而過。然後在大破壞行動執行時,主角才拼湊各式各樣的證據,發現自己就是泰勒的事實。
仔細想想,其實導演早已經把線索放在電影裡面。主角在自己的公司老闆面前自導自演毆打自己時,他的獨白是「我想起第一次跟泰勒在對打的時候」;主角也曾對觀眾說「泰勒有時候會替我說話」;雨中車禍的場景中,明明是泰勒開車,但最後翻車時,卻是主角從駕駛座爬出來。

最重要的線索應該是瑪拉,許多觀眾大概聽到瑪拉怒氣沖沖地指責主角的兩面性格時,就隱隱察覺了不對勁。那棟破舊的房子就是主角內心的投影,在泰勒跟瑪拉瘋狂做愛時,主角待在積水的地下室電源間,等待著能再度主控;在瑪拉質問主角為何有時瘋癲狂野有時冷淡疏離時,主角打開了地下室的門,泰勒坐在地下室,沉默地搖頭。一個人兒卻有兩盞燈彼此開關,而彼此開始爭奪主權的時候,也就迎來了終極的毀滅。
最後的結局尤其值得玩味,當主角對著泰勒說:「我的眼睛是睜開的。」然後轟掉自己的耳朵,昏迷前看到泰勒倒下,瑪拉則被會員押送到主角面前,這時主角睜開了雙眼,然後牽起瑪拉的手,一同觀賞著大破壞計畫成功執行,所有的信用卡總部跟銀行大樓被炸毀的末日風景。主角對瑪拉說:
「我們相遇的時機,剛好是人生最詭異的時候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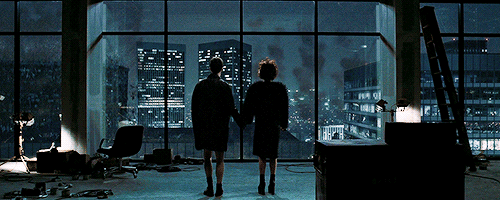
會做出這些行為,會說出這句話的人,到底是本來的主角性格?還是泰勒搶得了完全的主控權,以主角的身軀說話呢?其實想想這部作品一直有意識地維持雙重對立,一開始主角對泰勒揮出的那一拳,正中了泰勒的耳朵,而泰勒對主角耳朵的還擊,則在劇情的最後終於回敬。另一個證據是,泰勒與瑪拉的相遇(瑪拉服藥後兩人潛逃後徹夜做愛)比起瑪拉與主角的相遇(互助團體彼此爭鋒相對)明顯更加詭異。
然而無論是主角還是泰勒,那都是面對終末的某個顯影。可能我們面對自己乍看平靜無波卻一事無成的人生也是如此:總是偷偷渴望著有什麼意外發生導致死亡,或是在內心設想要砸爛所有事物拋棄一切。想要拒絕所有的追求與欲望,卻又不知道該獲得什麼,在內心不斷地爭鬥卻又徒勞無功。
我們是活在美麗新世界中的擱淺之人,只能憑著自己的想像來逃避或面對。不管是被動逃避或是主動面對,不管是絕望或是憤恨,那都是我們內心中的恐慌,我們的大破壞。是故鬥陣俱樂部永遠不會打烊,在這壞得像一灘爛泥,好得像一地黃金的時代裡,在所有空洞虛無的內心,屬於我們自己的那個人會時時刻刻,永劫無休地與內心的泰勒搏鬥著。白天與黑夜不一定會到來,我們只擁有,彷彿開始或是結束的黃昏或黎明。